有多少时光可以重来
3年,并不漫长,好像是昨天。
3年前的今天,我在30楼的会议室里和客户相谈甚欢,忽然之间头晕目旋,只见窗对面的写字楼左右摇摆。……地震了!我们迅速跑出房间,大楼摇晃中,外面大厅里所有人跑到洗手间,好几个女同事蹲在墙角哇哇哭。大家开始用手机做路灯走楼梯下楼,地面草地上聚满了人。忘记是谁一开始跟我说,重庆地震,我用手机拨鲁文电话,她接了电话说自己在沙坪坝某个写字楼5楼上毫无感觉,正朝楼下观望。我们还开玩笑说,不用跑了,如果真要死,就死吧,反正活着也没什么意思。后来,和几个同事坐在草地上吹了10多分钟的牛,再是保安说可以上楼了,大家一起坐电梯上去,刚回30楼,老板给我打了个电话:四川7.8级地震,快跟家电话。即刻给老妈打,第一次,没通,第二次,也没通。脑中出现坍塌老家的画面,双腿发软,心里念着,菩萨保佑我娘,我不想变成孤儿。第三个电话,终于通了。老妈说,她在家看电视,都没感觉,发现门在响,然后就跑院子里去,大家说地震了,摇晃了几分钟,没有大事。我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。
后来,知道是汶川地震。年少生活过的地方,想想很多认识的人也许就不再了。每天都在追着看各种各样的新闻,给所有能联系到的老师同学朋友打电话,有些人根本联系不上,平素也没有那么紧张过的电话另一端的人们,一个又一个绝望的消息,蔓延。后来的事情,逐渐平息起来。而最真切的感受,就是继05年初大白在宁波车祸之后,QQ上又增加了几个永远的灰色头像。他们的资料栏,写着再也不会变更的年龄和说明。
……S当时在C大读研,只是汶川的窝毁了。她在电话里跟我说,记了很多年的日记本,什么什么的……都没了。她说了很多伤感的话。我则安慰她,没了,没什么大不了。她说要我买了赔给她,我满口答应着。许多时光,都是流年。中间很多变故,来不及计算。我们都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故事若干。10多年,不知不觉的。我只记得老邮箱里躺着无数封S的信,每一年春节都会给我写一封,很长的文字,或者寥寥数语,好像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。我也习惯了。再是后来,基本没了电话,那些青涩的,都留在遥远的从前。我已经有些想不起来,大礼堂里跳锅庄的样子了。这个时间,草原上的花该是开的很娇艳的了吧。
5月7号,收到一个陌生号码落款是S的短信,内容是S当日升格当了妈,应该是她老公发的。我回两字:恭喜。惶然又陌生的。那幅白桦林,据说挂在他们家的墙上。有些人事,每当想起来,依旧是美好的,这样很不错。我想我是开始老了,掩饰不住的老了。
那一年,汶川红军桥头的KTV。S、让央、若巴……我们一堆人坐在黑呼呼的角落;那些年,奔在川藏路上疯狂的长途车摇摇晃晃;西羌第一村的腊肉,布洼寨早晨金色太阳照耀的羌碉;汶川的樱桃茂县的苹果金川的雪梨;赤不苏的小镇松坪沟的海子较场的穆桂英点将台和叠溪海子;桃坪沟羌寨遇见表演节目报幕的羌族美女,转年我们在八角碉藏寨再次碰面,她笑着朝我跑过来,说:我认识你。非要拉我跟着他们一起跳莎朗锅庄,我们聊的很开心,她说她在理县旅游局工作。那些年,我还是个剃着光头白皙瘦削的有些病态的穿破洞牛仔裤帆布板鞋大TEE挂在小身板上,背着双肩包和画夹的少年样子…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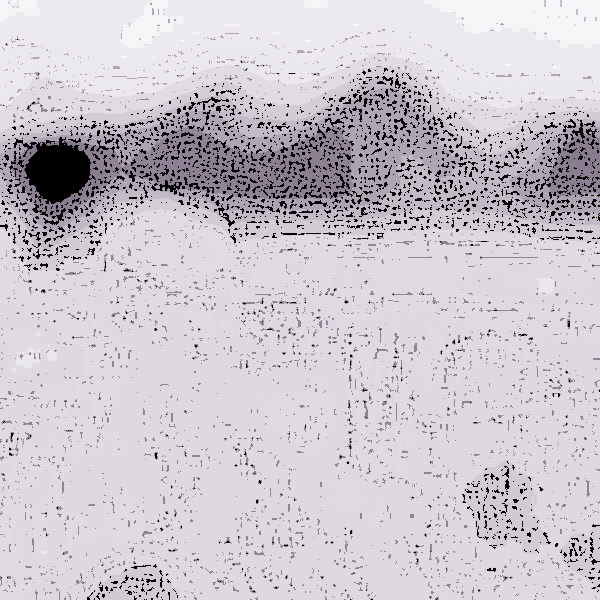
江湖又十年,从懵懂无知到确实无知,我走了好大一圈弯路,还在继续歪歪扭扭的路上。每天都在出发,每天都在问自己一些明显没有答案的问题,有时候也感觉到疲惫和心慌,但大多数时间,依旧是忙不迭的赶往下一站。不停的跟自己说,慢慢来,在不安中学着变老,在变老中学着淡然。还是有很多值得高兴的事情,NJ,跟你说呵,我的水仙花,就在昨天,它居然开花了。
提醒自己:
何时何地,都不能忘记最初的灯火,连同最后的湛蓝。
改变。
今天莫名其妙谷歌了一下,
发现自己胡扯的FINGO,意大利文是“假装”。
正合我意。








